“子弹飞过已八载,一步之遥竟四年”,2月5日,传了很久的姜文新片《邪不压正》放出预告后,立马引发了一波转发热潮。此前,姜文曾表示自己会在这部电影中再造一个老北京,再现昔日的北平。
《邪不压正》改编自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张北海几十年来围绕着纽约、北京这两个城市写作。他的“粉丝”中不乏文化名人:阿城、王安忆、王德威、陈丹青、张大春、骆以军……
《侠隐》讲述的是1936年的北平,青年侠士李天然,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随着他调查的深入,京城各路人马的斗智斗狠浮出水面,日本特务、亲日分子、豪门旧户、黑帮老大、交际花、外国记者等轮番上阵。而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悠悠然地过着,庙会、堂会依循旧例,东城、西城一如往日,人情冷暖、旧京风华扑面而来。然而卢沟桥一声枪响,北平淹没在战争烟尘中。
豆瓣上有评论说:张北海笔下的侠一点也不像侠,倒像个儒雅的绅士。而他笔下的北平却是我们走丢了的北平。
(以上内容部分段落摘自豆瓣,以下内容摘自《侠隐》原著,感谢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前门东站
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现在都快六点了,还没一点儿影子。
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灰灰黑黑一片,也早都认了。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不怎么吵,都相当耐心地站着,靠着,蹲着,聊天抽烟。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来回走动。不时有人看看表。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
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马凯医生。他个子很突出,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灰,精神挺好。
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来接人啊,马大夫?”马凯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可是仍然带点儿外国味儿的北京话回应,“是啊。”
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上海天津都少见。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不光是那些来这儿教书,传教,行医和开办洋行的,还有姘了中国女人的,来冒险发财的,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住上了一年半载,再两年三年,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也回不去了。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太好过了。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别说回国,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
马大夫就是这一种,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就和新婚夫人依丽莎白来到北京,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他就微微一笑,“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
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才吸了两口,一声笛响,一阵隆隆之声,一片欢叫。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东站。
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月台上一下子大乱。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喷着烟斗,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
他移动了几次,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月台上更吵更乱。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有的开口大骂,都他妈的是关外的车误点,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到了廊坊又等⋯⋯
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火车头嘶地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气,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马大夫看见了他。
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头发乌黑,脸孔线条分明,厚厚的嘴唇,稍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米色西装,没打领带,左肩挂着帆布背包,右手提着一只深色皮箱。
他也看见了马大夫,又走了几步,放下箱子,在嘈杂、拥挤、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伸出了手臂,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
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借光……”“劳驾……”“让让……”
马大夫伸手去接背包,“来。”
“我来。”
“那给我你的票。”
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人出去得很慢,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轮到他们的时候,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然后一指广场右前方,“车在街对面儿。”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
“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
他们左让右让,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洋车,板车,堆的行李,汽车卡车。
没多远,可还是走了快十分钟,才走到城墙根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上了前座。车站塔楼大钟刚过七点。
马大夫没发动,静了几秒钟,偏过头来,“摘下墨镜,天然,让我先看看你的脸。”
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眼镜。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又伸手推了推他的下巴,察看右脸,点了点头,“不错,连我⋯⋯不说都看不出来,”他顿了一下,“还满意吧?”
天然轻轻微笑。
马大夫发动了车。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还是那部?”马大夫点着头,慢慢开下小土坡,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儿的欧式东站的广场,上了东河沿。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再顺着电车轨道,挤在一辆辆汽车、自行车、洋车,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间,穿过了前门东门洞。

前门东站旧照
两个人都没说话。马大夫专心开着车,习惯性地让路,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他也不生气。天然坐在他右手,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黑福特刚过了东交民巷,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
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也没刮风。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七点多了,天还亮着,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天然摇下车窗,点了支烟,看见刚过东总布胡同没多久,马大夫就又右转进了干面胡同。
才一进,马大夫就说,“到了,十六号⋯⋯”同时按了下喇叭。左边一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马大夫倒了进去,“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的,还不错,两进。Elizabeth教书的美国学校,就在前面几步路。”
一出车房就是前院。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他们没走游廊,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
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再沿着墙边摆的茶几凳子,进了西边内室睡房。
“厕所在里面,你先洗洗,我在院子等你⋯⋯”马大夫顿了一下,面带笑容,伸出来右手一握,“欢迎你回家,李天然。”
是个白色西式洗手间。李天然放水洗了个快澡。出来发现他的背包皮箱已经给放在床脚。他围着大浴巾开箱找衣服。他不算壮。因为偏高反而显得瘦长。可是很结实,全身绷得紧紧的。他很快穿上了条藏青帆布裤,上面套了件灰棉运动衣,胸前印着黑色pacific College,光脚穿了双白网球鞋。出房门之前,又顺手从西装上衣口袋拿了包烟。
马大夫已经坐在院子西北角石榴树下一张藤椅上了。旁边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小圆桌,上面有个银盘,里面放着酒瓶酒杯,苏打水和一小桶冰块。
马大夫也换了身衣服,改穿一件中式黑短褂。李天然下了正屋台阶,抬头看了看上空的最后黄昏,坐了下来。
“Dewar’s?”
李天然说好。
“冰?苏打?”
“冰。”
马大夫加冰倒酒,递给了天然。二人无语碰杯,各喝了一口,而且几乎同时深深吐出一口气。
“回来了。”
“回来了。”
“高兴吗?”
李天然微微耸肩。
“有什么打算?”
李天然微微苦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呆呆看着手中摇来摇去的酒杯,冰块在叮叮地响。
“再说吧。”马大夫抿了一口。
“Yeah…. ”
二人静静喝着酒。一阵轻风,一阵蝉鸣。
“这是北平最好的时候⋯⋯”马大夫望着黑下来的天空,“过了中秋,可就不能这么院里坐了⋯⋯”
“这几年听见什么没有?”
“没有⋯⋯”马大夫摇摇头,“我来往的圈子里,没人提过。”
“再说吧。”
“再说吧。”
李天然轻轻一笑,“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也不见得。”
“怎么讲?”
“怎么讲?……”马大夫欠身添了点酒,加了点苏打水,“你们今天⋯⋯”
一个老妈子端了盏有罩的蜡烛灯过来,摆在桌上,“什么时候吃,您说一声儿。”
“刘妈⋯⋯”马大夫用头一指,“这位是李先生,丽莎和我的老朋友,会在咱们这儿住上一阵。”
“少爷。”刘妈笑着招呼,搓着手,转身离开。
马大夫等她出了内院,“你们今天这班车,为什么误点?”
“哦⋯⋯”李天然明白了,“你是说日本人?”
“日本皇军。”
“跟我有什么关系?”
马大夫脸上显出浅浅一丝微笑,“日本人一来,你那个未了的事,怎么去了?”
李天然闷坐在藤椅上,没有言语。马大夫也只轻轻吐了一句,“再说吧……”
李天然还是没什么反应。马大夫举起了酒杯,“不管怎么样,Maggie的事Elizabeth和我⋯⋯我们谢谢你⋯⋯还有,我们实在抱歉你吃的这些苦。”
天然抬头,“您怎么说这种话?那我这条命又是谁给的?”几声蛐蛐儿叫。天一下子全黑了。
刘妈又进了院子,“八点多了,开吧?”
马大夫看了看天然,“开吧。”
燕京画报
李天然一早就听见马大夫在外面打发老刘上胡同口去买吃的。他看看表,还不到九点,又赖了会儿床才去浴室。
他出了北屋,看见马大夫在院里喝咖啡看报。他站在台阶上抬头张望。
天空显得特别远,颜色深蓝,飘着朵朵白云。太阳穿过那几棵枣树斜射进来。他深深呼吸了几口清凉干净的空气,“Morning .”
“Morning.Beautiful day. ”马大夫指了下桌上的咖啡壶,“自己来。”
李天然过来坐下,给自己倒了杯。
“我要去西山住几天,”马大夫放下了报,“德国医院一位朋友在那儿租了个庄院,说丽莎不在,约我去过中秋⋯⋯你要去,我跟他们说一声。”
“不去了⋯⋯明天开始上班。”
“那你一个人过节?”
“过节?我几年没过了。”
“好吧⋯⋯我吃完动身,礼拜天回来。”
刘妈给他们上了马蹄烧饼和果子,还有酱肉。马大夫吃了两副,李天然三副。剩下一副,也是两个人分了。李天然添了杯咖啡,点了支烟,“马大夫,我也许看见了那个日本小子。”
马大夫一惊,“你是说⋯⋯”
“回来第二天逛街,就在西四牌楼附近⋯⋯绝对是他……那张圆脸我忘不了……”
“然后?”
“没有然后……就那一次,就那么一眼……”他顿了顿,“是命也好,是运也好,反正叫我给碰上了。”
马大夫皱起了眉头,“我那年回来,也替你打听过,可是没名没姓,只知道是个日本人,也无从打听起⋯⋯不过我倒问起过朱潜龙。”
李天然猛一抬头,看着马大夫,没有言语。
“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李天然沉默了一会儿,“不急,六年都过去了⋯⋯至少有一个在北平,还活着。”
“天然,”马大夫站了起来,“别忘了这是北平,也别忘了这是什么时候……到处都是日本特务,可别乱来,”说着就朝外院叫老刘上胡同口去叫部洋车,再回头对着李天然,“可别乱来……我该去换衣服了。”
李天然微微一笑,“放心。”这还是六年多来第一次如此清楚地听见大师兄朱潜龙的名字。
他送马大夫上了车,回到内院跟刘妈说今儿在家吃,不必张罗,有什么吃什么,又说还是院里坐,给泡壶茶。

旧时北平
除了东屋罩下来窄窄一片影子之外,整个院子给太阳照得发白,晒在身上挺舒服。李天然喝着茶,慢慢翻着《燕京画报》。
是按日期叠着的。每期像报纸那样两大张,对折起来,不过四页。创刊号是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四日,星期六。第一期第一页封面,除了一大堆公司商号的新年祝辞和创刊贺词之外,上方正中间是一幅旗衫美女全身照。下面两行说明:“北平之花唐凤仪小姐近影”,“北平燕京照相馆摄赠”。
广告可真多,不止三分之一。好像什么广告都有,而且平津两地都有。什么“美国鱼肝油,德国维他命”,“头痛圣药——虎标头痛粉”,“鲸鱼羊毛线”,“柯达六一六/六二○镜箱”,“味之素”,“天厨味精”,“‘奇异牌’收音机”,“西门子电器”,“大长城香烟”……妙的是,旁边又有则“赠送科学戒烟新法”广告⋯⋯还有什么“北平花柳病诊疗所”,还有“中原公司大减价,平津三店同时举行”,还有“‘双妹’老牌雪花膏,爽身粉,茉莉香,花露水”,还有“交通银行”,还介绍说它“资本收足一千万元,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 ……
内容还相当丰富,有文章,照片,图片,画片,全都是娱乐消遣性的。即使有关时人时事,也都涉及社会名流,像“汉口巨商陈仙老捐赠古物二千余件,价值四十万余元予湖北省书画助赈会……”,当然附加陈仙老的照片。要不然就是以照片报道社交际会,或仪式典礼,像“女青年会合唱团演出”,“扶轮社慈善茶舞”,“欧美同学会九名常任理事”,“中苏文化协会,中国美术会,中国文艺社,在京合办‘苏联镌版艺术展览’”。连河北省主席就职,都是以一排三张照片为主,文字只不过一行说明:“宋哲元在保定就职河北省主席。宋氏在保定下车时与欢迎者寒暄(右),召集所属训话(中),在操场对民众团体演说(左)。图中→所指为宋氏。”果然,图右宋哲元脑袋上一个黑黑的箭头……
有国画:“乾隆御题清丁观鹏摹宋人绘《渔父乐》”(中国借与伦敦中国艺术展者),有明星:“火车中阅报之影星胡蝶女士”,
有京戏:“坤伶红云霞之《得意缘》剧照”,竟然还有一张照片是“德籍女票雍竹君演坐宫时上装留影”,
有舞蹈:“日本宝冢少女歌舞团之两舞星”,
有摄影:《裸女》(美,保罗西顿),
有艺术:《少女出浴》(油画,孙炳南),
有时人素描:“即将回任之驻法公使顾维钧”,
有运动:“北平冰运健将丁亦鸣与周国淑女士”,
有风云人物:“我国女飞行家李霞卿女士在檀香山参观美国军用飞机场与我国驻火奴鲁鲁梅总领事及美空军司令麦丹路等合影” ……
偶尔还出现一两则外国影坛消息,也是一两句而已:“华纳影片公司现已与黛丽娥解约”。李天然念了半天,也搞不清这位“黛丽娥”究竟是好莱坞哪位女明星。

旧时北平
不过最使他觉得不可思议又莫名其妙的,是每期的“曲线消息”,像“(津)某二小姐,闻其爱人行将来津赛马,终日喜形于色”;“(平)某四爷有纳名舞女莎菲为小星说”;“(平)某二爷之少姨奶奶日前在某舞厅遗失手提包一只,内有数百元及绣名手绢一方,闻为一名小C者抢去,以作纪念云”⋯⋯妈的!大概只有其他某某某,才知道这几个某某某是谁——
“听老刘说您还没吃饭哪!”刘妈突然一句话,把李天然从画报世界中喊回来。
“还不饿,干脆再晚点儿,早点儿吃晚饭。”他发现刘妈胳膊上搭着一件蓝布大褂。
“南小街儿上瞧见了关大娘,说这件儿也好了。”
“就这件大褂儿?”他的心好像多跳了两下。
“就这件儿……夹的还早着呢……给您挂屋里去。”
李天然静了下来。很好,没提太阳眼镜,没交给刘妈一块儿捎回来。
这天晚上他睡得比较早,第二天起得也比较早。吃完了早饭,他从衣橱取出一条灰色西装裤,一件蓝衬衫,外面套上那件蓝布大褂儿。院子里的太阳已经很大了,还不到九点。他出门朝东往南小街走。
他没再犹豫,在虚掩的木门口叫了声,“关大娘。”过了会儿,又叫了一声。
“呦,是李先生。”清清脆脆的声音突然从他背后传过来。他转身,看见关巧红刚拐过小胡同那个弯儿,朝他走过来。还是那么干净清爽,蓝布包头,洗得快发白的蓝布旗袍儿,白袜子黑布鞋,左胳膊上挎着一个小菜篮儿。
李天然微微欠身,“我那副黑眼镜儿是不是落在你这儿了?”
“好像是……”她上来侧身推开了木门,跨了进去。李天然后面跟着,院子没人,又跟进了西屋。
关巧红把篮子放在方桌上,从个茶盘里拿起了那副黑眼镜,“是这个吧?”
他说就是,接了过来,“夹袍儿?”
“少个绒里儿,明儿上隆福寺去看看,给您挑一块儿。”
“不急⋯⋯对了,顺便找几个铜纽扣儿。”
“那还要等隆福寺……这儿没有现成的。”
“麻烦你了。”他告了别,才要转身出屋,关巧红伸手从篮儿里捡出一个蜜桃,塞到他手上,“刚买回来,您尝尝……”再跟着送他出了大门。
拐那个弯儿的时候,他戴上了太阳镜,眼角瞄见巧红还站在门口。
他出了烟袋胡同,咬了口桃儿。很甜,熟的刚好,汁儿也多,流得他满手都是。他沿着南小街往北走,还没到朝阳门大街就吃完了,手有点儿黏。在三条胡同口儿上,看见有家药铺门口摆了桶茶。一个拉车的刚喝完。他接过大碗也倒了点儿茶,喝了两口,又冲了冲手。
街上人不少。有的赶着办节货,有的坐着蹲着晒太阳。两旁一溜溜灰灰矮矮的瓦房,给大太阳一照,显得有点儿老旧。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儿,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李天然快十点到的九条蓝府。白天看得清楚。一座屋宇式暗红色大门。门外几棵大树。里头的树也看得见。灰砖砌的墙,还带点装饰。大门西边有个车房门。他上了三个台阶,红门上钉着一对大钢环,可是旁边门框上又装了电铃。他按了一下。
开门儿的是那个看起来快五十的听差,还是那身灰大褂,“李先生,这边儿请……”他半侧着身在前头引路,穿过前院,走进过道。西厢房的门半开着,听差的轻敲了两下。
一个女孩儿的声音说,“来了。”
“苏小姐,李先生到了。”
一位脸圆圆的小姑娘开了门,“李先生,您好。”白衬衫,黑裙子,言语形态一点也不忸怩。
圆明园废墟
十五号那天下午,李天然去灯市口那家自行车店租了车,背着帆布包上了大街。
他刚骑上去,还在人行道上,一声喇叭响让他抬起了头。几步路前头,一辆黑汽车差点儿撞上一辆洋车。司机伸出头来大骂。可是拉车的也偏头回了一句,“吹胡子瞪眼儿的干吗?有能耐打东洋去!”然后双手把着车弓子,没事儿似的,慢慢拉着那辆空车走了。
李天然看看没出什么事,就没再注意,只是听到汽车一上挡加油,顺便瞄了一眼。
是蓝田和一位打扮时髦的女人。只是短短一瞥,又只是上半身的上半截,他突然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可是立刻又觉得可笑。才回来没几天,就只见过这么几个人,或许是时髦人士的打扮都差不多,看起来眼熟。他没再去想,原路骑去了海淀,还是住进了“平安客栈”,还是那间西屋。
他进了客栈就没再出去。晚饭也是打发伙计叫了碗面在屋里吃的。九点,他开始准备,跟大前天晚上夜行的装扮一样。只是因为天冷,又更阴了一点,上身多了件黑皮夹克。他又从帆布包里取出前两天买的一支手电筒,试了试,插进了裤口袋。十点,他吹熄了油灯,闪身出了屋门,轻轻带上,在黑暗之中观察片刻。
有几间屋子还透着亮,也还听得见前头柜台那边传过来的人声。可是他没再犹豫,吸了口气,蹿上了房。
海淀正街上还有好几家铺子没关门,灯光挺亮,不时还有部汽车呼的一声飞过他的面前。他在街这边等了等,过了马路,顺着朝北的那条大道走去。燕京大学校园的灯光老远就看得见。路上偶尔还碰到一双双,一对对的学生。他不去理会,正常稳步地走他的路。

旧时北平
天很黑,也有点湿,像是要下雨。过了燕京没一会儿就瞧见了清华校舍远远的亮光。他这才开始注意看路。
他很快找到了那个三岔口,上了折向西北那条。又走了一会儿,拐进了小土路。再没多久,他摸黑绕过一堆残石,进入了野地。
四周很暗,云很低很厚,只是天边一角偶尔透出一小片惨白,使他勉强分辨出三步之内的乱石、苇草和洼地。他不敢用他带来的电棒,只好慢慢一步步迈。鞋早就湿了。无所谓,只要不踩进泥沼就好。
他几乎撞到那根石柱,用手摸了摸,盘算了一下方向,找到了上回坐的那块石头。可是他没停,又朝前走了二十几步,在另一个不到半个人高的石座那儿打住。他看了看表,浅绿时针说是十一点零五。石头座很潮,他就蹲在旁边,四周张望了一下,什么也看不见,风声有点凄凉。他耐心沉住气地等,也不敢抽烟。
他知道这么黑没有必要,可是还是掏出那条黑手绢,蒙上了下半截脸,又把帽檐拉到眉毛。就算五步之内认不清,可是万一来的不是师叔……是朱潜龙反而简单了,就此了断……可是要是万一是别人,误打误撞地来了个全不相干的别人……那还是不能就这么露相露脸……
他一身黑地蹲在黑夜之中,觉得整个这档子事,这个背了六年的血债,最后怎么个了法,就跟这片漆黑荒野一样渺茫。五年前来过那么多回,一无收获。那今夜呢?他尽力不去多想,就知道越是去想,那前景就越像这黑夜一样,伸手不见五指。
再看表已经差十分十二点。他感到心在跳,再一次用尽目力四周查看。
唉……六年了……还会有人赴这个约吗?师叔和大师兄说不定早都死了……再看表,还差三分。
他眼不眨地注视着那浅绿荧光分针慢慢移到了十二。
他深深吸了口气,“啪”地一声轻轻一击掌。然后从一数起……八、九、十。
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掌声。
他的心快跳出来了。
再又数到十,这回稍微多用了点力,“啪”!……八、九、十——
“啪!啪!”
两声清脆的击掌。他偏偏头,好像从他右上方过来。
李天然的心快炸了。他尽力沉住气,眼睛向掌声方向搜过去,心中慢慢数到十,回击了一掌,站了起来,往前一跃,压低了嗓子,“哪位?”
“什么人?”
声音有点沙。
李天然不再迟疑,“师叔?”
对方稍微停顿片刻,“再不回话,我可要动手了。”
李天然觉得暗中人影一闪。他本能地倒错半步。一道白光照亮了他上半身,逼得他眼睛睁不开。
“师叔?是我,大寒。”
他打开电棒,上下左右一扫,伸手拉下蒙脸。
他的电棒也找到了对象。
是个矮小的老头。
模样儿有点熟,他还不敢认,往前跨了一步。
下巴一撇短胡,清瘦的脸,两眼有神。这才把记忆中的师叔和面前的老头对上,“师叔?德玖师叔?”
小老头也用电棒上下照了照天然,“大寒?”
李天然关了手电筒,往前迈了三步,叫了声“师叔!”跪了下去。

旧时北平
老头儿也关了手电筒,搀起了李天然,把他搂在怀里。两个人在黑暗之中紧紧抱着,谁也没说话。许久,许久,老头儿放开了手,往后退了一步,单膝下跪,双手抱拳,低着头,“掌门,太行派二代弟子德玖拜。”
李天然一阵恐慌,扶起了师叔,在暗夜里盯了面前黑影片刻,“您来了多久?”
“半个钟头吧。”
“好在是一家人……”李天然感到惭愧,“就一点儿什么也没听见……您在哪儿?”
“后边破石头门上头。”
李天然抬头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那您知道我在哪儿蹲吗?”
德玖没接下去,拉着天然走到石阶旁边,伸手摸了摸,有点湿,可是还是坐了下去,“我没瞧见你,也不知道你在哪儿躲着,也不知道谁会来……咱先别去管这些了,要紧的是,咱爷儿俩这回碰头了……我问你,”他拉天然坐下,“这回是你头次来?”
“不是……出了事以后,我来过总有十次……您哪?”
“我?这回是连着五个月五次。”
“您是说您以前来过?”李天然心头一震,“真就没碰上?”
“是啊……来过……三年多前,那回也来了有半年多。”
李天然心头又是一震,几乎说不出话来。真是阴错阳差。他紧紧握着师叔的手。云好像薄了点儿,斜斜天边呈现出大片淡白,勾出了废墟一些模模糊糊的轮廓。面前的师叔身影,也可稍微辨认出少许。他有太多的话,又不知从哪儿说起,“您是什么时候听说的?”
“十九年九月出的事?”
“是。”
“那是出了事之后……我看……一年多快两年我才听说……我那会儿正在甘肃。一听说就赶了过来。话传得很不清楚……反正那回我赴了七次约,谁也没碰见……”
李天然心中算了算,十九、二十、二十一,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那他已经在美国了。
“……这边儿也没人知道内情,只听说从火堆里捡到了四条烧焦的尸首,两男两女,也不知道是谁活了下来……这回是过了年……可是也不知道会碰见谁……你哪?……”
“这回还是头一次⋯⋯我上个月才回的北平。”
“好,这都先别去管了。这次能碰上可真……唉!”德玖顿了顿,“要不是你师父当年有这个安排,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该上哪儿去找谁。”
李天然也叹了口气,“说的是……要是没这个安排,我也真不知道该怎么,该上哪儿去找您……可是……”他突然有点紧张,“可是,大师兄也知道这个初一约会……不知道他来过没有……”
“不知道,我上回来了七次,这回五次,都没碰见他。”
“我上回……我看,四年多前吧,一共来过九次,也没遇上他。”
“好!”德玖一拍大腿,“至少他还没咱们爷儿俩的消息,也不知道咱们今儿晚上碰上头了……很好,这些待会儿再聊⋯⋯你在哪儿落脚?”
“海淀,平安客栈。”
“好……我这回住在西边一个庙里,不太方便。咱们上你那儿去说话……这儿别待太久。”
“这就走吧。”李天然先站了起来,扶起了师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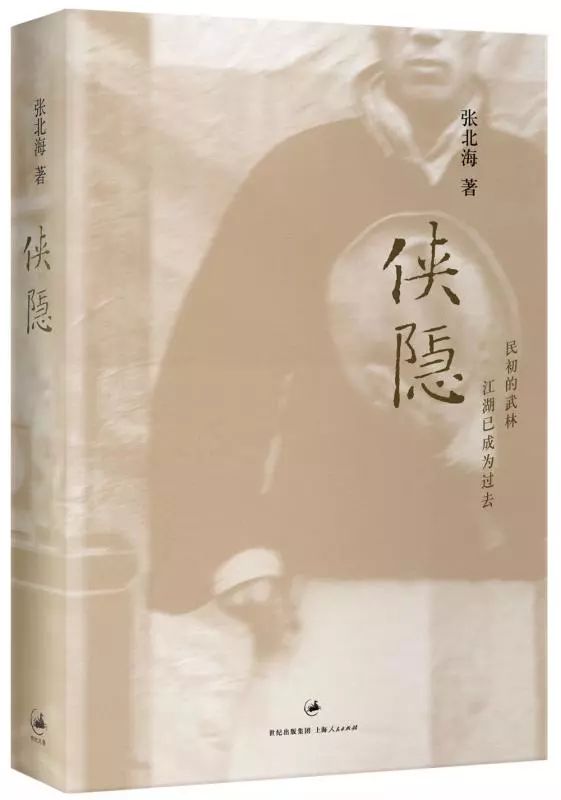
《侠隐》
